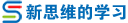穆旦(1918年4月5日-1977年2月26日),原名查良铮,曾用笔名梁真,生于天津,祖籍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,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,中国现代主义诗人、翻译家,九叶诗派成员之一。[1][2]

穆旦6岁即发表习作,青年开始诗歌创作,之后一直寄情于现代诗;联大毕业后,曾参加了中国远征军;1952年,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;1953年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;20世纪四十年代接连出版《探险队》《穆旦诗集(1939~1945)》《旗》三部诗集;1977年,因心脏病突发去世[3][4]。
中文名穆旦
籍贯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
国籍中国
民族汉族
出生日期1918年4月5日
出生地天津
毕业院校美国芝加哥大学
曾用笔名梁真
性别男
代表作品探险队、穆旦诗集(1939~1945)[5]、旗
职业诗人、翻译家
主要成就在大公报和文聚上发表诗作
逝世日期1977年2月26日
本名查良铮
配偶周与良
人物生平
1918年4月5日(农历二月二十四日),出生于天津。与作家金庸(查良镛)为同族的叔伯兄弟,皆属“良”字辈,[6]有亲属关系。
1929年,入南开中学读书,从此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,开始写诗。当时日寇侵凌,京津首当其冲,穆旦写下了《哀国难》,“洒着一腔热血”大声疾呼: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,/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!/眼看四千年的光辉一旦塌沉,/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!”1935年,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,半年后改读外文系,抗日战争爆发后,随学校辗转于长沙、昆明等地,并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副刊和昆明《文聚》上发表大量诗作,成为有名的青年诗人。
穆旦在这里继续探索和写作现代诗歌,并在《清华学刊》上发表。他写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,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,又有很强的现实感。
1937年七七事变后,10月随大学南迁长沙国立长沙临时大学,后又徒步远行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。同年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副刊和昆明《文聚》上连续发表《合唱》《防空洞里的抒情诗》《从空虚到充实》《赞美》《诗八首》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。
1939年开始,系统接触西方现代派诗歌、文论,创作发生转变,并走向成熟。
1940年,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,留校担任助教,负责叙永分校新生的接收及教学工作。
1942年2月,投笔从戎,24岁的穆旦响应国民政府“青年知识分子入伍”的号召,以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,在副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5军司令部,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。同年5月至9月,亲历滇缅大撤退,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,于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穿山越岭,扶病前行,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。
1943年,回国后经历了几年不安定的生活。
1945年,创办沈阳《新报》,任主编。9月,根据入缅作战的经历,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著名诗篇——《森林之魅——祭胡康河上的白骨》,另有相关创作《阻滞的路》《活下去》。
1947年,参加后来被称为“九叶诗派”的创作活动。
1948年,在FAO(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救济署)和美国新闻处工作。
1949年8月,自费赴美留学,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、俄罗斯文学。
1952年6月30日,毕业,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。
1953年初,自美国回到天津,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,致力于俄、英诗歌翻译。
1958年,受到迫害,调图书馆和洗澡堂,先后十多年受到管制、批判、劳改,停止诗歌创作,坚持翻译。
1975年,恢复诗歌创作,一举创作了《智慧之歌》《停电之后》《冬》等近30首作品。
1976年3月31日,右腿股骨颈折断。
1977年2月26日春节期间,穆旦于凌晨心脏病突发逝世,享年59岁[7]。死前,穆旦在《冥想》的诗中道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:“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,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,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,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。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。”
1979年,平反[8]。
主要作品
| 作品 | 时间 |
|---|---|
| 穆旦诗文集[9] | 1996年 |
| 穆旦诗选 | 1986年 |
| 旗 | 1948年 |
| 穆旦诗集(1939-1945) | 1947年 |
| 探险队 | 1945年 |
| 冬 |
| 作品 | 时间 |
|---|---|
| 穆旦译文集 | 2005年 |
| 英国现代诗选 | 1985年 |
| 唐璜 | 1980年 |
| 欧根·奥涅金 | 1957年 |
| 普希金抒情诗集 | 1954年 |
其他作品
| 作品 | |||
|---|---|---|---|
| 爱情 | 理想 | 友谊 | 春 |
| 流吧,长江的水 | 赞美 | 理智和感情 | 停电之后 |
| 智慧之歌 | 哀悼 | 玫瑰之歌 | 奉献 |
| 童年 | 春天和蜜蜂 | 听说我老了 | 春底降临 |
|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[10] | 五月 | 黄昏 | 冬夜 |
| 玫瑰的故事 | 我 | 秋(断章) | 秋 |
| 自己 | 两个世界 | 发现 | 我歌颂肉体 |
| 我看 | 诗八章 | 园 | 出发 |
| 在旷野上 | 感恩节——可耻的债 | 自然底梦 | 他们死去了 |
| 夏 | 赠别 | 还原作用 | 面包 |
| 牺牲 | 我的叔父死了 | 森林之魅——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| 裂纹 |
| 哀国难 | 诗 | 有别 | 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 |
| 悲观论者的画像 | 野兽 | 更夫 | 活下去 |
| 苍蝇 | 轰炸东京 | 寄后方的朋友 | 诗二章 |
| 通货膨胀 | 老年的梦呓 | 神魔之争(长诗)——赠董庶 | 被围者 |
| 打出去 | 诗四首 | 隐现(长诗)让我们看见吧,我… | 农民兵 |
| 不幸的人们 | 先导 | 蛇的诱惑——小资产阶级的手势之一 | 华参先生的疲倦 |
翻译作品
| 作品 | |||
|---|---|---|---|
| 波尔塔瓦 | 青铜骑士 | 普希金抒情诗集 | 普希金抒情诗二集 |
| 欧根·奥涅金 | 高加索的俘虏 | 加甫利颂 | 云雀 |
| 雪莱抒情诗选 | 唐璜 | 拜伦抒情诗选 | 拜伦诗选 |
| 布莱克诗选 | 济慈诗选 | 别林斯基论文学 | |
代表诗作
《赞美》
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,河流和草原,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,鸡鸣和狗吠,
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,
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,
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,
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。
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:
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,沉默的
是爱情,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,
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,
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;
我有太多的话语,太悠久的感情,
我要以荒凉的沙漠,坎坷的小路,骡子车,
我要以槽子船,漫山的野花,阴雨的天气,
我要以一切拥抱你,你,
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,
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,佝偻的人民,
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。
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。
一个农夫,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,
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,许多孩子的父亲,
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
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,
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,
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,
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。
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,
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;
在大路上人们演说,叫嚣,欢快,
然而他没有,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,
再一次相信名词,溶进了大众的爱,
坚定地,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,
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
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,
他没有流泪,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。
在群山的包围里,在蔚蓝的天空下,在春天和秋天经过他家园的时候,
在幽深的谷里隐着最含蓄的悲哀:
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,许多孩子期待着
饥饿,而又在饥饿里忍耐,
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,
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,一样的是
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,
而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。
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,
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,
因为他,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,
痛哭吧,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,
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。
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,
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
无尽的呻吟和寒冷,
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,
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,芦苇和虫鸣,
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。
当我走过,站在路上踟蹰,
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
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,
等待着,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,
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,
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。
1941年12月
《哀国难》
一样的青天一样的太阳,
一样的白山黑水铺陈一片大麦场;
可是飞鸟飞过来也得惊呼:
呀!这哪里还是旧时的景象?
我洒着一腔热泪对鸟默然——
我们同忍受这傲红的国旗在空中飘荡!
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,
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!
眼看四千年的光辉一旦塌沉,
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;
坟墓里的人也许要急起高呼:
“喂,我们的功绩怎么任人摧残?
你良善的子孙们哟,怎为后人做一个榜样!”
可惜黄土泥塞了他的嘴唇,
哭泣又吞咽了他们的声响。
新的血涂着新的裂纹,
广博的人群再受一次强暴的瓜分;
一样的生命一样的臂膊,
我洒着一腔热血对鸟默然。
站在那里我像站在云端上,
碧蓝的天际不留人一丝凡想,
微风顽皮地腻在耳朵旁,
告诉我——春在姣媚地披上她的晚装;
可是太阳仍是和煦的灿烂,
野草柔顺地依附在我脚边,
半个树枝也会伸出这古墙,
青翠地,飘过一点香气在空中荡漾……
远处,青苗托住了几间泥房,
影绰的人影背靠在白云边峰。
流水吸着每一秒间的呼吸,波动着,
寂静——寂静——
蓦地几声巨响,
池塘里已冲出几只水鸟,飞上高空打旋。
1935年6月13日
《冬》
1
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,
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;
才到下午四点,便又冷又昏黄,
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。
多么快,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。
我爱在枯草的山坡,死寂的原野,
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,
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,
不知低语着什么,只是听不见。
呵,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。
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,
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,
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,
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。
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。
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,
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,
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,
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,
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。
寒冷,寒冷,尽量束缚了手脚,
潺潺的小河用冰封住了口舌,
盛夏的蝉鸣和蛙声都沉寂,
大地一笔勾销它笑闹的蓬勃。
谨慎,谨慎,使生命受到挫折,
花呢?绿色呢?血液闭塞住欲望,
经过多日的阴霾和犹疑不决,
才从枯树枝漏下淡淡的阳光。
奇怪!春天是这样深深隐藏,
哪儿都无消息,都怕峥露头角,
年轻的灵魂裹进老年的硬壳,
仿佛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。
3
你大概已停止了分赠爱情,
把书信写了一半就住手,
望望窗外,天气是如此萧杀,
因为冬天是感情的刽子手。
你把夏季的礼品拿出来,
无论是蜂蜜,是果品,是酒,
然后坐在炉前慢慢品尝,
因为冬天已经使心灵枯瘦。
你拿一本小说躺在床上,
在另一个幻象世界周游,
它使你感叹,或使你向往,
因为冬天封住了你的门口。
你疲劳了一天才得休息,
听着树木和草石都在嘶吼,
你虽然睡下,却不能成梦,
因为冬天是好梦的刽子手。
4
在马房隔壁的小土屋里,
风吹着窗纸沙沙响动,
几只泥脚带着雪走进来,
让马吃料,车子歇在风中。
高高低低围着火坐下,
有的添木柴,有的在烘干,
有的用他粗而短的指头
把烟丝倒在纸里卷成烟。
一壶水滚沸,白色的水雾
弥漫在烟气缭绕的小屋,
吃着,哼着小曲,还谈着
枯燥的原野上枯燥的事物。
北风在电线上朝他们呼唤,
原野的道路还一望无际,
几条暖和的身子走出屋,
又迎面扑进寒冷的空气。
1976年12月
《诗八首》一
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,
你看不见我,虽然我为你点燃,
哎,那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,
你底,我底。我们相隔如重山!
从这自然底蜕变程序里,
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。
即使我哭泣,变灰,变灰又新生,
姑娘,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。
二
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,
而我们成长,在死底子宫里。
在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形的生命
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。
我和你谈话,相信你,爱你,
这时候就听见我的主暗笑,
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
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。
三
你底年龄里的小小野兽,
它和青草一样地呼吸,
它带来你底颜色,芳香丰满,
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。
我越过你大理石的智慧底殿堂,
而为它埋藏的生命珍惜;
你我的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。
那里有它底固执,我底惊喜。
四
静静地,我们拥抱在
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,
而那未形成的黑暗是可怕的,
那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。
那窒息我们的
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,
它底幽灵笼罩,使我们游离,
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。
五
夕阳西下,一阵微风吹拂着田野,
是多么久的原因在这里积累。
那移动了景物的移动我底心,
从最古老的开端流向你,安睡。
那形成了树木和屹立的岩石的,
将使我此时的渴望永存,
一切在它底过程中流露的美,
教我爱你的方法,教我变更。
六
相同和相同溶为疲倦,
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;
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,
我驱使自己在那上面旅行。
他存在,听我底使唤,
他保护,而把我留在孤独里,
他底痛苦是不断的寻求
你底秩序,求得了又必须背离。
七
风暴,远路,寂寞的夜晚,
丢失,记忆,永续的时间,
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
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——
呵,在你底不能自主的心上,
你底随有随无的美丽形象,
那里,我看见你孤独的爱情
笔立着,和我底平行着生长!
八
再没有更近的接近,
所有的偶然在我们间定型;
只有阳光透过缤纷的枝叶
分在两片情愿的心上,相同。
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飘落,
而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,
它对我们不仁的嘲弄
(和哭泣)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。
1976年12月
感情生活
1949年12月,在佛罗里达州与正在生物系留学的周与良结婚[11]。
人物纪念
穆旦葬于北京万安公墓。[12]
2018年4月5日,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南开大学文学院举办了查良铮(穆旦)先生百年诞辰暨诗歌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。[13]
人物评价
穆旦早在四十年代就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,他的诗在上海诗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。四十年代初期,闻一多遍选《现代诗钞》时,选入了他诗作十一首,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一首。1948年初,方宇晨的英译《中国现代诗选》在伦敦出版,其中就选译了穆旦诗九首。1952年,穆旦的两首英文诗被美国诗人赫伯特·克里克莫尔(Hubert Creekmore)编选入《世界名诗库》(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)同时入选的其他中国诗人只有何其芳。穆旦诗作的艺术风格、诗学传统、思想倾向和文学史意义,在四十年代就被一些诗人和评论家较为深入地讨论着,并被介绍到英语文学界。
五十年代初以来,穆旦频受政治运动的打击,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,被迫从诗坛上销声匿迹,转而潜心于外国诗歌的翻译,直到骤然去世。穆旦去世多年以后,才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。人们出版他的诗集和纪念文集,举行“穆旦学术讨论会”,给予他很高的评价。“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大师”的排行榜上,他甚至被名列榜首。这种种的不寻常,被称为“穆旦现象”。
袁可嘉在《诗的新方向》中认为,穆旦“是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、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”,现在看来这一判断是准确的。袁可嘉回忆了现代文学史上现代化新诗潮的由来和发展,认为“穆旦是是站在40年代新诗潮的前列,他是名副其实的旗手之一。在抒情方式和语言艺术‘现代化’的问题上,他比谁都做得彻底”。不过袁又指出,这样的“彻底性”难免在某些尚不成熟的诗作中带来一定程度的生硬和晦涩,使他的作品到今天还不能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欣赏,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。
王佐良认为“无论如何,穆旦是到达中国诗坛的前区了,带着新的诗歌主题和新的诗歌语言,只不过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迟迟地不来接近他罢了”。王佐良还谈到了穆旦晚年的诗作,认为诗人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坎坷,仍有那无可企及的诗才。他认为《冬》可以放在穆旦最好的作品之列。
轶事典故
1934年,查良铮将“查”姓上下拆分,“木”与“穆”谐音,得“穆旦”(最初写作“慕旦”)之名。
爱国意识
穆旦的救亡意识非常浓烈,“有一次,社会上抵制日货,穆旦就不让母亲买海带、海蜇皮吃,因为当时这类海鲜大多是从日本进口的。要是买来,他不仅一口也不吃,到头来还把它倒掉。因此连大家庭中的伯父们也议论穆旦是赤色分子,让他三分。”
“有一分光,发一分热”,从青年时代起,鲁迅的这句话成了穆旦最喜欢的名言。
“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”,据说这是穆旦自己经常对人对己说的话。
相关推荐
最新文章